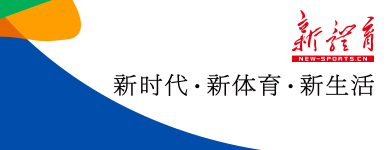体坛时评丨人生最“巅峰”的感动
珠穆朗玛峰,世界第一高峰。我们很多人都听过与珠峰有关的故事,去年《攀登者》电影上映,更是为每个人心中种下了一个珠峰梦。作为一名登山专项记者,我时常被前辈的故事感动,也时常会采访到登山英雄,只是没有想到会在今年跟随2020珠峰测量登山队来到珠峰脚下,体会到在世界巅峰的感动。
4月底到达拉萨后,海拔高度也开始一天天提高,拉萨(海拔3650米)—日喀则(海拔3850米)—定日协格尔(4300米)。终于,5月5日来到了海拔5200米的珠峰大本营。还记得抵达大本营的那天,我心里除了兴奋,还有担忧。兴奋的是终于可以膜拜到“第三女神”的面容,担忧的则是人人都会遇到的高反问题。虽然一路一点点适应着海拔,但是5200米的高度,比我此前去过最高的青海湖还高出了1000多米!
从定日到珠峰大本营,首先要翻越嘉措拉山,最高5248米已经让我体会到了高海拔的滋味。而100多道大弯道更是把人摇晃得受不了。终于,看到了绒布寺,这是游客大本营的标志。而继续再往深处行驶7、8公里,登山的大本营终于到了。
珠峰似乎近在眼前,美丽、壮观、神秘、圣洁,所有美好的词汇都不足以形容看到珠峰的感觉,但呼吸真的“不友好”,据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介绍,这样的海拔,氧气含量只有平原的50%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在北京呼吸一口的氧气,在这里要连呼两口才能接近。因此,大本营的休息帐篷里总会放着血氧仪和血压计,谁不舒服就赶紧去量一下数据。但是和大家设想中不太一样的是,来到大本营的人很少有吸氧的,因为那样属于“降低海拔”,对于适应高原没有好处。
吃过午饭,分配好帐篷后,我来到了自己的帐篷里。帐篷里有一张简易床,上面铺好了垫子。我打开羽绒睡袋,钻进去休息。身上的三件抓绒加上羽绒服都没有脱掉,棉线帽子也戴在头上,但还是冻得瑟瑟发抖,帐篷边被风吹得呼呼直响。一个下午我也没有睡着,再加上高反,头疼欲裂,浑身无力。

提早入住大本营的中登协领导以及队员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新来的成员。晚饭时,大本营“营长”薛云给了我一粒头疼药,可以缓解头疼。登山队员蔡卿给我送来了一床电热毯……居住条件改善了,但是上厕所还是个大问题。大家说喝热水可以缓解高反,但是一到下午六七点,就不敢再喝水了,要不然半夜起来,顶着冷风跑到室外去上厕所,那种滋味也实在不舒服。
在大家的关心和照顾下,我终于过了艰苦的第一夜,夜里不知道醒了多少次,睁开眼看下表:12点多、凌晨两点多、3点多、5点多……据说是因为氧气不足睡觉会憋醒,那就继续使劲喘气,努力接着睡。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照镜子,给自己吓了一跳——脸好像肿了。大本营的“营友”们看了一眼,平静地说:“是呀,昨天一上山你的脸就肿着呢。”
5月6日,我在大本营的第二天,2020珠峰测量登山队出发了。我一边忙着采访队员,祝愿他们早日登顶返回,一边心里盘算着在大本营熬过一周就解放了。没想到,天公不作美,运动员连续经历了两次下撤,三次攻顶。5月27日成功完成任务,29日下撤,我在大本营足足住了24天!
但这20多天的大本营生活,相信会成为我一辈子的珍贵记忆。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太多的感动:前线总指挥王勇峰在第二次下撤之后茶饭不思,研究天气和队员登顶的情况,血压高到一天要吃两次降压药;总协调张志坚和大本营“营长”薛云,4月就来到大本营与队员并肩作战,两人的血压一度都高达170,但他俩只是抽空下山调整两天,随后又回到大本营坚守到最后一刻;登山队长次落,在前期没有适应的情况下,成功登顶并坚持在顶峰测量150分钟,下撤时体力透支最终选择在7028米营地休息;攀登队队长袁复栋,在7028米行军至7790米营地时遭遇大风,队员们搭建一个多小时才搭好帐篷,为了怕帐篷不被吹走,他们六七个人挤在一顶帐篷里,用背包和后背顶住帐篷,为了保证重力仪等测量设备不损坏,袁复栋将重力仪挂在帐篷中间,抱着设备坐了一夜;还有“90后”登山队员蔡卿,作为支援组组长,他原本的职责是守候在6500米营地,但是7028米需要测量,他就冒着流雪危险赶到7028米,并不断呼唤队友们注意流雪,最终气管着凉,好几天都咳嗽不止……
太多太多的感动瞬间,如此真切地在珠峰上演着。登山人就是这样,热血爱国,坚强如铁,兄弟情深,使命必达。登山中心主任李致新每天给前方打电话了解情况,在登顶后更是从北京赶到拉萨为队员们庆功,亲手为大家送上鲜花和哈达。
珠峰测量登山活动已经结束,次落和袁复栋脸上的冻伤也开始结痂……但在大本营的日日夜夜,跟随登山采访过程的点点滴滴,将成为我一段终生难以忘怀的记忆,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之中,它也将不时地被打开,不时地被回味,成为我今后人生道路当中的鞭策,人生当中最深刻的记忆。
图片来源:中国体育图片